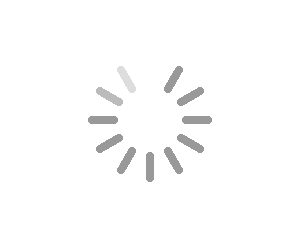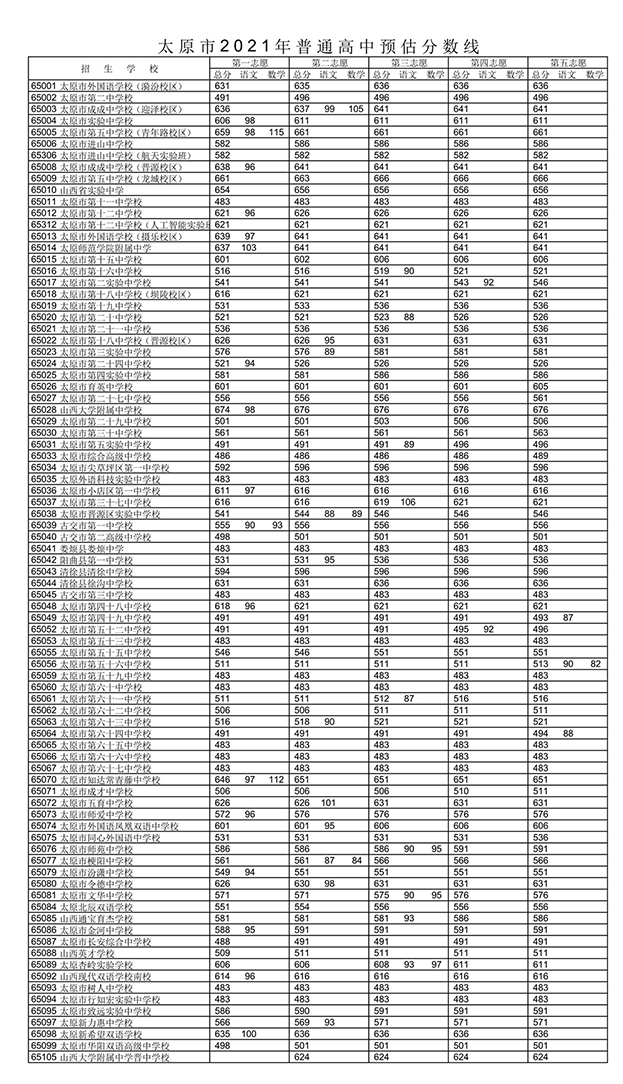阿里河虽然是旗政府所在地,但人口没有大杨树多,考生也少。等候在考点外的家长,简单寒暄后,很快便熟络起来,他们大多都来自大杨树,用各自孩子的名字介绍自己。
6月7日这天,鄂旗的最高气温升到了接近30℃,开始有了高考的感觉。考场外,办手机卡的摊位和一家整形机构支起两顶帐篷,提供一些塑料椅子。母亲们聚在这里,谈论的多是孩子的学习,还有未来的工作。
有人担心自己孩子偏科,“有一科秃噜,成绩哇就下来了”,有人对谁家的孩子“分配”到了哪儿津津乐道。
男人们站在树荫下,或者干脆就在太阳底下晒着。孩子是妈妈的事,他们似乎更愿意分析今年的收成,预测粮价的涨跌,或者中美关系的走向。但只要有人开了头,话题会立刻转移到孩子身上。
“小家伙啥都不跟我说,咱也不知道孩子的想法。”一个男人笑着自嘲。他是个年轻的父亲,穿着T恤和牛仔裤,黝黑的皮肤和指甲里的泥土,证明着他庄稼人的身份。
接着,男人就自责起来。他是大杨树邻镇人,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大杨树陪读,上面还有父母,“都靠我一人养活”。平日里,他待在屯子里守着田地,农闲时就开着四轮子“收铁”(回收废铁)。
“我对孩子的学习关心太少了。”高考前,他向妻子了解孩子的模考成绩,得知在本科线附近徘徊。他想起自己年轻时,初中毕业后父亲就让他下学,“想抱孙子”。现在,“孙子长大了,搞不好还是得种地。”
说什么都来不及了。“考好了给你宰只羊”,他用自己的方式鼓励儿子。
事实上,在不少家长眼里,种地也是一件不错的营生。
大杨树镇的面积相当于一个中部县的大小,这里的田地用“垧”来计量,一垧相当于15亩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现在这代中年人的父辈,陆续从东北其他地区来到这里拓荒。开垦到哪里,田地的边界就在哪里,少的十几、二十垧,多则上百垧。
这里雨水充沛,不用灌溉,肥沃的黑土地几乎是全国最适宜农作物生长的地方。庄稼种下,“喷点药就完事儿”,一年下来,“忙里忙外也就两个月的时间”。
去年大豆涨价,一垧地净收入7000元左右。就算遇到坏年景,一垧地也能落下3500元的国家补贴。
“只要有点儿地,整天除了喝就是玩。”一个在考场外等候的男人如此形容自己的生活,“镇上那些走道儿不利索的、坐轮椅的,都是喝酒喝的。”
他似乎对这种状态不太满意,又无力走出。
“咱们这代人能对付过去,下一代人咋办?”他看着考点的大门,声音低沉。
有时候,让年轻人接班种地,也是件一厢情愿的事。那个年轻的父亲担心,现在的孩子没下过地,“种不好”,也不愿意当一个农民。
他曾威胁过儿子,上不好学就回家种地。儿子告诉他,“只要把地给我,我马上给你卖了”。
王全友没有参与这场讨论,他一直站在墙角,沉默着。他家只有17垧地,自己干了半辈子,勉强撑起了家庭,下半辈子的路,一眼就能望到头。
他倾尽全力,希望孩子能有更多可能性。他和妻子都赶到阿里河陪考,面对儿子,他们努力保持从容,尽量露出笑容,但又不知道要说什么。
这两天中午,王全友来到同一家餐馆。每天他都点三碗冷面,要份免费的咸菜,解决一家三口的午饭。
二中
在呼伦贝尔市,大杨树二中是仅有的一所公办乡镇高中。
镇上很多人都能讲出这所学校的辉煌历史,那些故事总能与清华北大,以及另外一些如雷贯耳的大学名字联系起来。
这里的升学率吸引着整个鄂旗,还有隔壁旗几个乡镇的生源。就算哪个班级出现了来自200公里外甘河林业局的同学,也不会有人为此感到惊讶。
除了高中,镇上还有5所小学和4所初中。超过1万名在校生,让大杨树成为鄂旗当之无愧的教育中心。
大杨树街上,“三蹦子”(三轮摩托车)是最常见的交通工具,一共有1.2万多辆。它们统一刷成红色,再装上车棚,去镇子任何地方都是3元钱。这些“出租车司机”里,很多都是陪读的家长——做饭之外的时间里,这几乎是最灵活的生财之道。
到了冬季,这里的天下午3点多就会黑透,二中的学生们要上7个小时的“夜间课”。换作其他东北小镇,这样的季节里,晚上7点后街上就很难见到行人。但在大杨树,每天晚上9点半晚自习下课时,二中门前那条路都会堵车,围满接学生的家长。
一部分学生不会回家,而是要赶去上晚上10点到11点的补习班。在广袤的大兴安岭森林里,这里可能是为数不多还在亮灯的地方。
大杨树仅注册备案的校外培训机构就有19家。一座名叫“学府佳苑”的小区,底商的LED广告屏上,正滚动播放着“提分班”的热线电话。实际上,哪怕在镇上某条偏僻街道,也能找到挂着“××教育”招牌的补习机构。
教育也带动了大杨树的房地产经济,几栋在建的新楼盘,都不约而同地选址在二中附近。陪读家长一般会在镇上买下,或者至少租下一套房子。离学校近的最紧俏,通暖气的楼房租金需要9000元一年,车库也可以住人,要8000元,7个月的供暖费通常要租户承担,7000元。
只要离学校足够近,就连没暖气的平房也会抢手。王全友租住的平房,每年租金6000元,烧煤要3000元。若是普通年景,他一年能收入7.5万元,王飞虎补3门课,一年的补课费需要3.5万元,再加上一家人吃穿,剩下不多少。
但是,每年只有秋收,卖了粮食后才能拿到现钱。他们往往先把田地抵押给银行,拿到贷款,把儿子补习班的钱交清,再用来年的粮款把贷款还上。
在这个围绕着教育运转的镇子里,二中校长苗孔新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。
他在大杨树做了十几年中学校长,开始在林业中学,那时的林中和二中还是旗鼓相当的对手。
后来,很多南方城市的学校带着“安家费”“人才房”找上门,一些经验丰富的班主任和骨干任课老师一起“组团”出走。
再后来,林中没落,高中部并入了二中。他刚调去二中,又遇到了生源问题,镇上每年中考前100名,会被市重点高中“掐尖”录取走,哪怕这部分学生要到500公里外的海拉尔或者牙克石念书。他的一位好朋友,女儿考上了呼和浩特的重点高中,离家近2000公里,“比上大学都远”。
作为一所乡镇高中,师资的问题依然没能解决,去年学校招聘物理教师,结果报名数不到3人,最终因为达不到开考条件半途而废。
在学校里,苗孔新是那种让学生们“讨厌”的校长,上课时他经常突然面无表情地出现在窗外。下课时,看到调皮的孩子,他也会忍不住训上两句,“把聪明劲儿都用到学习上”。
去年,有很多中小学都放了假,他坚持照常上课。有学生在网上发帖抱怨,他被叫去教委谈话,他理直气壮,“你们又没发通知让停课,怎么能随意放假”。
“这边不比内地,我们节奏慢,生活过得安逸,学生们就没什么压力。”他知道学生都害怕自己,但又坚持那样做得对。
得知学生们评价“校长很负责任”时,他有些惊讶,然后点了点头,笑着不断回味。
他相信升学率是对孩子们最好的回报。去年,大杨树二中的本科上线率是72.2%,这个数据几乎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两倍。
南方
高考结束,学生们需要真正思考“去哪里”的时间到了。
早有人盯上了这门生意。考试那两天,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成为考点外的焦点。他声称自己是一家停产厂子的车间主任,已经钻研高考志愿十几年,在现场推销志愿填报服务。
在围观家长面前,他并没有着急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,而是先谈起了一次南方之行的经历。
“义乌为什么会成为国际物流中心?”他突然向家长们发问,然后扶了扶头上的鸭舌帽,上面印着清华大学的校徽。
这似乎激起了围观者的兴趣,他变得有些兴奋起来,开始向家长们介绍自己在那里目睹的种种“奇观”。他努力解释自己对“南方”的理解,似乎要告诉大家,自己见过真正的南方,了解南方的运行逻辑。
方法奏效了,有些家长频频点头,“人家是见过世面”。不多会儿,他手里的名片就分发完毕。
多远才算南方?可能每个大杨树人都能给出不同的答案。
有人觉得沈阳就算南方,有人觉得南方“至少要过了山海关”,还有人坚持有海的地方才能叫南方。
有时候,“南方”只是他们想要探索世界的渴望。一个女生立志要考到郑州,她没去过这座城市,只是在地图上看到它纵横交错的交通网。
王飞虎想去上海,因为它“最大、最繁华”。他去过最大的城市是齐齐哈尔,那是高三上学期,他起了荨麻疹,爸爸带着他去看病。
“一进市区,我就看到了高楼。”现在提起这段经历,他仍然难掩激动,“我数了数,一共21层。”
在很多家长眼里,“南方”意味着规则和希望。
提起南方人,几乎每一个大杨树人都会承认,“人家就是比咱们这边人精明”。虽然“精明”时常会成为一种被他们嘲讽的特质,比如将它理解为“斤斤计较”,但他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去“南方”,“学学人家怎么想”。
王全友支持儿子报省外的大学,他答应儿子,即使考不上上海的大学,也会带他去上海看一看。
那些从大杨树走向南方的孩子,最终也给家乡带来了回报。几个二中的毕业生,在南方读完大学后,又回到二中任教。曾经坐专列去高考的学生,如今成了火车站的售票员和站务员,为这趟列车服务。
一群当年考到北京的学生,在牵线北京西城区与鄂旗的对口扶贫中,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高考过后,大杨树又恢复了宁静,二中校园的高三教学楼没有了读书声,黑板上的高考倒计时停留在了“1天”。一位毕业班班主任更新了微信签名:在电脑里新建了一个文件夹,准备迎接下一届学生。
火车站的汽笛声还是会准时响起,大杨树站客运主任程显敏也恢复了重复且琐碎的工作。两个月多后,大学开学季就要到来。他相信一定会有许多新面孔,他们从这里出发,踏上新的人生旅程。(记者杨海文并摄)
(文中王全友、王飞虎为化名)
文章来源于:http://gaozhong.ljyz.com.cn 高中网
网站内容来源于网络,其真实性与本站无关,请网友慎重判断